脚趾头裂口子怎么办
小 说

◆
◆
◆
◆
◆
棠 棣
女,69年秋生于昌江之畔。
江西省作协会员。
一生痴爱文字,沉溺于笔耕,
发表散文、小说等四十万字。
多篇作品入选文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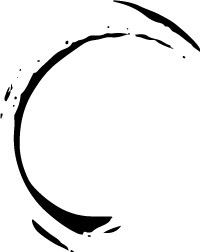
决 堤

1
松晧躺在工棚里看星星。星空象一只巨大的锅反扣在大地上。星星点点的闪烁的光芒向地平线上撒去,象种得不均匀地种子出的苗,疏密无规则,银河里密匝匝,其他地方东一块西一块。没有星的地方从松晧的眼里看去,特别幽深。苍蝇树挂满了一条条树蝇子,杨树哗哗作响,而更远处那棵孤柳,在夜色下婷婷玉立,守候着一阵阵夜凉。江水很安静,看不见的凶险潜藏得很深。蛙声焦燥不休。松晧拍拍几声,拍了一手蚊子血,虽然点了蚊香,到底没有什么用处。饥肠辘辘的蚊子时刻伺机攻击祼露的肌体。
一夜平安无事。洪峰还在路上。
浑身酸痛,松晧平摊开身子,想起昨晚的一幕,仍然有点胆寒。那时他正沿堤察看,预报中的洪峰将在二十五小时后到达,堤上一个个年轻的战士席地而卧,顾不上拧干军装上的泥水与汗水,沉沉睡去了。他们各自做着梦,鼾声与梦呓从年轻的身体里象气泡一样冒出来。他们确实是太累了,一次次抢险,折腾得这些年轻的军人疲惫不堪。他想起远在广州读书的儿子,也正是这个年纪,他大约正在宿舍里做梦吧。这个年纪的孩子个个养尊处优,个个是父母的心肝宝贝,他们的父母如果看着他们如此吃苦受累,一定十分心疼。这些孩子真不容易。而他此刻并不能为他们做什么。昨天,儿子来电话,叫他注意安全,注意身体。能记挂父母,就已经算懂事的啦。当时他努力掩饰声音里的疲倦,大声地说:你放一百个心,抢险一线都是解放军,我只是巡视,并不累,也没什么危险。
堤坝加固工作已经完成,洪峰没有来之前,大家可以休整一下。然而他却心里毛刺刺地,不知道哪里不对劲,无法安睡,不停地在堤坝上走来走去。接连下了几天的雨之后,河水暴涨。大家都紧张而疲惫。
他越走越远,路过二队守护处,细斗他们正在“斗牛肉”。生产队还是叔公手里的事,叔公在的时候,即便分田到户了,遇上有任务要分组干活时,还是按原来的生产队分。他是叔公的铁粉,虽然现在的人早没有生产队的概念,他也愿意以此来分组,把圩分成几截,一个队分管一截,每队派人看守自己负责的一截圩。
二队守护的地方,正是当年叔公舍身抢险的地方。那是多少年的事啊?那是86年,记得他当时还是个初中生,跟水娣同班。那时水娣多水灵啊,带露水的花骨朵似的。那年整个暑假他都因为惦记水娣夜不能眠。那夜也是这么闷热难当。他坐在煤油灯下看书。村子里很寂静,人都上堤坝上抢险去了。留下的老弱病残只是默默地搬家,跟蚂蚁一样无声无息。狗闹的锣声显得十分凄厉:咣,咣,咣。狗闹无奈地喊:大家都听清楚啦,圩要倒啦,老人孩子能上楼的快上楼,能搬走地快搬走。咣咣咣。狗闹拖声曳气,从村东走到村西,又从村西走到村东。其实村子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,能上圩的都上圩去了。几个看家看孩子的老人正往松晧家门口搬东西,松晧家地势高,那都是住在低处的邻居抢救家财。松晧坐不住,就跟奶奶说:我要上圩去看看。奶奶正帮忙邻居拿东西,停下手来拦住他:你爹妈让我看住你,你别瞎跑。况且你一个猴娃子,肩不能挑,手不能提的,抢圩也使不上劲。你看你的书去,我们家水淹不了。
我看看我妈去。松晧知道大人们都十分宝贝他,话没说完一溜烟跑了,丢下奶奶在门口跺着小脚。他是独子,家里人宝贝他,也把他看得紧。到了前畈上,只见灯火点点如繁星,到处人声嘈杂,人影晃动,整个前畈的菜地都挖得乱七八糟,平时为一株菜能争得面红耳赤,为一锄地吵得口沫横飞的人,今天谁的地都顾不了,什么菜也不要了,什么都豁出去了。男男女女,挑土的挑土,灌沙袋的灌沙袋,场面浩浩荡荡,万亩田畈周边几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到圩前,村与村,人与人,在灾难的威胁面前,尽释前隙,抱成一团。灾难是衡量人性的尺度,也是支撑人类共进退的纽带。松晧前前后后跑了一圈,看见水娣也在灌沙袋,就上去帮忙。绕舌的妇女们都没有多少话了,她们只管手忙脚忙地干活,人人都拼命似的。水娣的脸色在混乱的夜色中看上去很苍白,大约也像自己一样被这种悲怆氛围震慑了,被绝望的情绪所扼制了。他们也不说话,那个时候的男女同学本是很少说话的,上了初中后,原来一起长大的他们,便开始在人前拉开距离了。他们不说话,松晧挖土,水娣装土,配合默契地装沙袋。
突然圩上一阵慌乱地喊叫。有人惊问:倒了吗?有人开始往喧哗处跑。正在惊慌失措时,有人喊:叔公让水冲走了。叔公是水娣的爹。身边的水娣听后一声悲嚎:爸。丢下手里的锄头就跑,松晧也丢下畚箕追过去。他拉起水娣的手在高低不平的地里奔跑。到了缺口,只见叔公正被人扶着,一身落汤鸡。原来圩堤决了一个口子,只见水很快把缺口冲大,叔公拎起一只沙包跳了下去,想用身体堵住决口,但水势太横,一下把叔公冲走了,一径冲远,冲进圩内的菜地。而叔公一跳下去,后面几个后生也跟下去,决口边一只鱼船上的鱼网被拉了下去,终于又把决口堵住了。一场虚惊。
那个夜晚铭刻在心里,再也丢不掉了。后来……后来水娣却嫁了别人,不,是招了别人。松晧叹了一口气,在圩外一个树墩上坐来下抽起一支烟。
突然听见有人嚷嚷:不玩了,我看见松晧过来了。
别别别,赢了钱就不玩了!别找借口。另一个人着急地说。
真的刚看见松晧来了,我们得巡视去。
你赢花了眼吧,再来一把再来一把。
松晧听着他们扯皮,索兴不理会,沿着堤坝慢慢检查起来,大家都让这几天的紧张弄得十分疲乏,让他们玩会休息休息吧。
洪水在月光下倒温顺,河面比平日宽阔了很多,水声隐隐约约。他用手电仔细地扫视水边,只见一堆堆浮物从上游下来,有树枝,有木板,有死鸡,倒没有见到死猪。那是什么?一个小旋涡?他急急地跑上圩,到另一边一看,果然有个渗水口。忙喊道:
细斗,你们快来。有漏。
松晧水性好,喊一声也不等他们过来就下水去,摸索水下,果然有一个漏口,还好及时发现了。险呀,洞口很快就会被越冲越大,成为缺口。大家都围上来,松晧指挥他们抱稻草,小心地用草填塞,又里外用沙袋堵上。忙乎了好一会才妥当。留下两人看管,其他的人也不敢歇息,分头再四处巡视。松晧说大家一定要上心,有险情官兵们冲在前头,我们也得让这些孩子歇歇。巡视就我们自己来。大家都是经验老到的人,一定要盯紧,发现险情立即报告。
松晧把村里负责的圩都巡视完了,天就快要亮了。各队的人都换了一批。他也累了,准备再躺会儿。闭着眼却总想着水娣。儿子说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个曾经爱过又得不到的女人,那女人最终成了心里的朱砂痣眼中的白玫瑰。这小子大出息没有,说起这些倒一套一套的。嘿嘿,大约水娣真是我心里的朱砂痣眼中的白玫瑰。这个说法合我心。我的白玫瑰在干什么呢?她一个人在家带着三个孙子,还种几亩田地,真是够累的。她身体历来弱,这洪水逼到家门口了,男人和儿子们都没回来,也没人心疼她。那个男人是一惯弱,凡事都得水娣一个女人家上前拿主意。那两对儿子媳妇,又只知道在外面打工赚钱,到底是钱要紧还是人要紧?等有机会我得跟那俩小子说道说道。
水娣横竖是受苦的命,想帮也帮不上。也就是在心里头想想,一辈子只想想。想想就一辈子了。那天见水娣正在田里打药。天上太阳火烈鸟似的,水娣却长衫长裤,头上扎着毛巾,正在禾田里来回地走,一边吃力地压着喷雾器。他走上前去,把喷雾器拉下来背上,说:你看你死要强吧,这个是女人干的活吗?你跟我说一声我顺便给你打上不就行了吗?
水娣尽他去打药,一边坐在田埂上擦汗:什么都劳动你,劳动得过来吗?
我现在好歹也是支书,照顾你还不是一句话。
多谢你的美意。
你还是要见外。从来你就对我见外。
不见外行吗?你屋里宁的嘴跟刀子似的,我犯得着给自己添堵!
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你别理她就行。
水娣不说话,从水沟里洗把毛巾擦脸。
打完药,他们一块在水塘边洗手。水娣把毛巾洗干净递给他说:擦擦。他却心猿意马起来,看着她胸衣口脱开的扣子说:水娣,你的身材还是那么好,皮肤还是那么白,你还是那么——美。他斟酌了一下,没有用好看而是用了美字,好看是可以随便用的,好看也是经不起岁月的,美却不可以随便用,是经得起时间消磨的,是永远都好看。用年青人的话说美是走心的,是用心感受的。男人活了几十年了,年过半百,喜欢,动心,都不是难遇的事,但爱,却不是轻易的事。他从来不对水娣说喜欢她,就连那个“爱”字,都只含在嘴里,年轻时没有说,现在更不敢轻易说。他觉得自己又象年轻时一样嘴拙起来,脸也红了。
水娣看了看他,低头扣上扣子说:别废话。真的,我一直把你放心里。废话。真的,当年我就是太怯了,不然我早娶你了。废话。早知道你嫁别人过得不好,还不如我娶了你。废话。我们那时太听父母的话了,一个村前后脚就到,有什么招亲不招亲。废话。真的,早知今日,我当初就非要了你,我们非在一起了,生米煮成熟饭了,他们还能怎样。废话!唉,我晚上去你家好吗?你就给我开一次门好不好?水娣却不再说“废话”两个字,一把夺回毛巾要走。他强拉住她:别走,我们都老了,再晚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她生气地说:老都老了,儿女都大了,丢不起这个人哩!可是你知道我一直心里舍不下你,尤其是你过得不好,我心里时刻惦记你。好不好是我自己的事,你惦记也是白惦记。水娣背上喷雾器在稻田中走远去了,她扭动的腰肢渐渐消失在田垄。
身下一片燥热。一股无名之火已经聚集成一股力,一股攻城略地的蛮力。水娣不要走,水娣不要走。
松晧被身体里的力撑得清醒过来,翻身起来,拿起一瓶矿泉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去。再拿一瓶水抹一把脸,淋湿毛巾擦了擦脖子。
松生在边上看着他笑,几天没回家了,是不是想嫂嫂了?天亮了,离洪峰到还有些时间。你放心回去洗个澡,我在这里盯着。
松晧心里想,家里倒不必牵挂,地势高,早又吩咐过老婆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得去水娣那边看看,她家地势低,她一个女人家,没依没靠的,不知道家里安排好了没。
2
松皓想着嘴里就应了一声,那我回去一趟,一会就来。骑上摩托车,一脚发动起来,加上油门冲了出去。
突然手机响了。他松开油门摸出手机。
什么?倒了?哪里倒了?前塘倒了。前塘是长堤内五个村之一。妈的,到底没保住。行了,我知道了,通知大家赶紧撤,躲大水,注意安全。
他的心里突然涌上少年时的那个抢险之夜的悲怆。想起那夜他拉着水娣奔跑地亡命感觉。虽然现在国家救灾力度大,灾区不愁挨饿受冻,但水患历史性的创伤留给水乡人的集体意识仍然让他不胜悲伤。大家已经纷纷向村里跑去。官兵也在撤离。电话又响了,老婆在电话里大声说:圩已经倒了,你们也不用守,快回家吧。他忙说:家里都安排好了吗?老婆在那边大声责怪道:哎呀,大支书现在才记得问家里安排,等你记起家早冲到乌拉国去了,放心吧,没指望你大支书,我全安排好了。没给你拖后腿。那就好,你看着家和娃娃们,我安排下村里的事再回。说完也不等老婆说话,挂了电话加大油门冲了出去。
缺堤的水来势太猛,水娣家地势最低,在村东,离缺口最近,他必须抢在洪水之前到她家,帮她转移到楼上去。可是他还没到路口,水头已经冲了过来,他只得调头从另一条路过去,还是迟了,水头又迎着他过来。他无路可走,只能直冲,迎着水头冲上去,想在水尚不深的时候冲过去。水却越来越深,车越行越吃力,终于,冲力与浮力一下连人带车掀了起来。他挣扎着站稳,只能扔下车子趟过去了。
水娣家大门洞开,院里已经进了水,凳子,衣服,杂物七零八落地浮在水上。水娣水娣你在哪?他一个个房间闯,一边叫唤,心里七上八下一团乱晃。楼下所有房间都没人应他,他的声音急促起来。来到厢房楼梯口,才见水娣抱着一只箱子跪倒在楼梯上,看来是跑上跑下多趟,已经精疲力竭了。他跳过去抱起她:水娣水娣。悲伤与怜惜顷刻间从心头冲到眼里,冲到鼻腔,冲到咽喉。水娣的眼泪也缺了堤,紧紧抱着他哭了起来。水娣水娣别怕,我来了,我打你电话你不接,真急死我了。水娣哭得象个委屈的孩子。小孙子们呢?水娣指了指楼上,嘴里呜呜咽咽。那就好,人没事就好,东西淹了就淹了吧。别哭,别哭。他亲了亲她满是泪水的脸,你别哭呀。又亲她干裂的嘴唇。你哭我心疼。又亲她涂抹着灰土的脖子。宝贝宝贝,你别哭,让我疼你。我这辈子的遗憾就是没机会疼你。他把她贴在墙上,一点点地亲吻她,小心地爱抚她。他想把内心的怜惜从嘴里一股脑都送达她的心田。这一切,曾经只是他心里翻腾过千万遍的臆想。他如一个美梦成真的少年一样激荡。水娣就象一朵迟开的迎春花,在他怀里开放起来,临风摇曳。她疯狂地迎合他,纠缠他,任由他在她身体里掀风作浪。仿佛一场洪水把她的茧泡开了,她化茧成蝶了。仿佛洪水是一只丘比特利箭穿透了厚厚的时间,终把两颗心射穿了,串了起来,紧捆一起。仿佛曾经遗落的爱的种子,www.czybx.com突然发了芽,冲破生活里层层的封锁不屈不挠地生长HmWMtsitt。这一场洪水把他们冲进往昔,他们在过去的时间里找到珍藏多年的爱,终于热烈地相爱起来。
他们是一对被选中的动物,不明就里上了爱的方舟,并在方舟里看着世界的沦陷与生命的浮沉,在洪荒的等待中安慰对方爱抚彼此。
迷乱中脱下的衣服已经被水俘获,正在水里或浮或沉,人已经被逼上台阶的拐角。惊涛骇浪之后的平静里,他还紧紧地抱着她,轻轻地咬着她的耳朵。水娣水娣为什么你是纯女户?喔,纯女户。水娣水娣我要不是独苗多好。喔,独苗。水娣水娣缺堤了。喔,缺堤了。水娣水娣家里淹了。喔,淹了。水娣水娣,东西冲走了。喔,冲走了。
松皓拒绝了水娣给他拿来的干净衣服,他从洪水里捞出自己的衣服穿上,却不知怎么出去。村子被淹了,他这个支书却陷落在水娣这里,村子里平平静静,没有多少人的村子比以往更静。他打算趟水出去,却见隔壁的满红叫他:过来过来,你媳妇跟儿子刚挣禾斛过去,你从我这边走。松皓从两家的楼顶跨过去,下了满红的楼,满红拖出一只大木盆,他找出一根木棍,坐上木盆,抬头看见水娣依着二楼的栏杆,脸色潮红,目光闪亮。
刚出门就见老婆良姨和大孙子划着禾斛过来了。良姨见她从满红的院子出来,顿时火起:你个老骚棍,我到处找你,你果然就到了这个骚精家里。
满红邪着眼看良姨:喏,你自己看不住男人,怪谁呀。
良姨就要上去扯满红,满红也不躲,松皓见楼上已经没有水娣了,也不管她们,爬上禾斛就要走,良姨赶紧丢下满红趟着水撵上去。
满红浪笑着道:看紧你的男人,通村没几个男人在家,一村的女人都骚情着,你看得住吗?
良姨不敢站起来,紧扶禾斛扭头回骂道:你个不要脸的骚精,没人要的婊子。松皓回头望了望,见水娣再也没出来,不免心烦,对良姨低骂一声:闭上你的臭嘴,老子这个时候不到处巡巡,村里出了事谁负责。良姨就不吱声了。
3
水娣在阳台上见对面阳台上的满红,不免心虚,忙要进屋,满红却叫住她:水娣婶,你这没良心的,我帮你担了这污名,你不谢我也罢,还躲我。
水娣站住,笑着把手里端着的豆子伸过栏杆给满红,满红抓了把豆子,撮几粒放嘴里嚼,斜眼看着她:松皓想你也不是一两天的事,你们的事大家都知道。水娣一听惊恐地把眼睛问住她。满红笑道:不是这事,是你们以前的事。水娣的心才落回去。
满红咯嘣咯嘣吃着豆子,关不住嘴:良姨最防的也就是你,松皓只有对你是真心的,只要你肯答应松皓,他怕是家都不要了。
水娣忙说:别瞎说。
满红就笑:瞎说什么,是你一直不肯理他,他跟全村的女人睡,念叨的却都是你。
水娣不着声,半响说:那又怎么样。想起自己躲了一辈子,到底没躲掉,以后怎么办呢?这种事传到良姨耳朵里,岂不是要被她骂街。传到儿女耳朵里,是要羞死他们哩。
不免有些仓皇,眼里就落下泪来。
满红说:你就是太想不开!不要说松皓一表人才,我们家里的男人长年在外,一村子老弱病残,哪还有几个周全的男人,女人常年打饥荒,哪个不眼吧吧盼松皓,看不得良姨那副志高气扬的。看你把她比下去,大家心里都痛快哟。她也就是在你面前摆不起来。不过,她要知道你们的事——你们昨天的事,也不轻饶你的。就是不要让她知道,你们的事——你们昨天的事也没别人知道,我不会出卖你的,你让松皓每次来都从我家走,我不怕那个老乞婆,她来我家相骂也不是一两回,我不怕她。满红又说,我晓得的,你也不是不爱松晧,你就是怕良姨撕破脸皮,你就是太要脸面。我来给你们遮掩,我不怕。
水娣知道,满红是个直肠子女人,在她眼里,天下男人只有两种,一种是用来爱的,一种是用来蔑视的。前者可以为之赴汤蹈火,后者为她付出一切她依然不屑。所以满红肯为了松皓讨好水娣。但满红的过于体己,水娣听得满心不情愿。她借故水开了脱了身。
松晧没有再来,他正忙于接待各方慰问,发放救灾物资。洪水已经退出了屋,在院子里汪着。乘着水没退远,水娣带着孩子们里里外外清洗了两天,总算把家里清扫干净了。这几天的劳累,倒让她心里清静了几天。可人一坐下来,焦躁又上了心头。
她盼着见松晧,又怕见。她知道有些东西碎了完了,就像她那从姑娘时就收藏的一对接吻瓷人碎成碎片了。但与碎瓷不同的是,这种完又不仅仅是毁灭,又有些什么长了出来。不毛之地长出一些嫩苗苗,不知道是庄稼还是杂草。庄稼还是杂草都不打紧,那娇嫩的生命就足以让人怦然心动了,让灵魂蠢蠢欲动了。不过骚动更像暗夜的烟火,照亮了一个人的孤寂。
松晧忙着救灾,接待各方救灾的人,发放救灾物资,他们没有时间私会。他从围墙外丢进来的几条鲢鱼,投进的一捆蔬菜,让人带来的米面及其他,都是带着隐秘的温度,让她的心里燥一阵凉一阵。她觉得自己病了,成了一个打摆子的人。
孩子睡着了,她独自在二楼阳台乘凉,闷热中蚊虫猖獗,她不紧不慢摇着蒲扇,似乎是睡着了。她听见松晧的脚步来到大门口,听见他轻轻地推门。她没有动,手机叮一声,屏幕上闪出一行字“松晧:开门”。她没有动,听见满红开门的声音,听见满红说:从我家过去。松晧说,我看水娣在不在家。
满红说,在的。
她睡了吗?怎么不开门?
你以为全世界女人的门都为你留着呀!也只有我随时候你跟候皇上一个样。
别闹,我要从你这边爬过去。
你个没良心的,我什么事没听你的,也只有我敢明着跟你,你跟我睡就睡,你让我拉皮条我就拉皮条。我为你做红娘你就这样对我。
好了好了,你等我回来找你。
好吧,我知道你只爱水娣,而我是最爱你的女人,你却只能娶良姨。他妈的全是扯淡。
就你话多,等着给我开门。
水娣轻轻退回屋,把门关上了。她听见松晧推不开她的门,又爬回到满红的阳台。她依着门听着他们在阳台上拉扯。她知道松晧不是她一个人的,从来不是,也永远不是。她也不会只属于松晧,她是一个被划分成块的蛋糕,父母丈夫儿女子孙,他们一块块取走了,留下的支离破碎的部分,她已经分了一块给松晧,她再也给不了太多。她常常梦见少年的松晧拉着她逃跑,她总是跑不动。两个人逃不走,就分开逃吧,她想。一个人,也许她还是逃不了,但至少松晧不需要拖着她,不要被她拖累。错过就是有错过的理由,回头去找比当初的错过更错,错得离谱。她混混沌沌过了一夜。
早上,满红想过来跟她说话,她借口有事回避了。她不是吃满红的醋,她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,只有逃离。
松晧夜夜来找满红。他是在生她的气了。他用这个法子来折磨她。
满红说,你这样让松晧伤心了。他最近瘦了//www.czybx.com好多。
满红还打算劝她,她说你别跟我提他。
满红说,看不出来你这么心硬。
水娣心里说,事情很快会过去的,当初他们的恋爱受阻,她以为自己会死,最后不是各自安好吗?如今都儿孙满眼了,他也有了那么多女人,不在乎少她一个。
跟水娣松晧一起受煎熬的还有良姨。夏天还没过完,良姨已瘦了一大圈,找满红吵了三架后,她没了主意。村里的女人都好对付,她们都不敢公然与她这个支书夫人对战,但满红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女人,她年轻健康,男人在外打工,她独自在家带孩子,哪里耐得住寂寞。性格泼辣也就罢了,他的男人完全管不住她。找到她婆婆告状,婆婆来到她家还没开口,她先叫上板了:你管好你儿子,他才是你拉出来的。因为儿子在外地也有女人,婆婆张不开口说她,赶紧退出来回家。良姨对女儿说,你爸爸以前也沾花惹草,都不是这个样子的,我看他这次心真走了咧。
儿女不敢明说爸爸,只能说妈妈你看淡点,我爸他又不是不顾家,男人跟沙一个样,你越抓紧漏干净。
松皓发的消息一条接一条,水娣看了马上把消息删除了,也不回话。
你到底要我怎样?你要我离婚吗?
水娣不回复,她是为爱情死过一回的人,一个人只可以为爱情死一回,一次就够了,她不能再死去活来了。
你再不理我我就开诚布公了,我告诉全村人我们好了,我们要在一起。
水娣慌忙回过去一句话:那你就直接杀了我。
4
冬天的太阳暖暖地铺满院子。水娣把被子都抱出来晒了,又来到老姑的小屋,把老姑的被子也抱出来晒好,就陪着老姑秀鞋垫。老姑跟水娣不沾亲,老姑是苕茅的老伴。苕茅年轻时因为成分不好,一直打光棍,直到老姑抛弃一双儿女跟了他。老两口一直住在两间厢房里,没有亲友没有子女,两个人平静度日。近年老姑腿脚因为风湿不太方便,但视力还好,天气好就坐在门口绣鞋垫,绣的鞋垫十分精致好看。水娣每天都抽空过来陪她坐坐。
老姑突然说,满红的坟头长了草了,这女子,可惜了。
水娣打了个寒战。是的,满红死了。事情本来发展不到这一步的。那天日子十分平常,水娣看着满红出门,她说去街上买衣服。她一脸朗朗的,完全不像生关死劫就在眼前的人。路过松皓家门口,良姨就隔了院墙骂“妖精”。满红回骂:有本事你也妖啊!拴不住男人的心你怪谁。良姨跳脚骂道:我不跟你一样做婊子,你男人不养你赖着我男人养。满红气急起来:谁要你男人养了?我没有用你男人一分钱,我们是爱情你懂吗?爱情!良姨以手划脸,跺脚羞她:狗X爱情!满红叫道:我就是爱他,爱他到死,死也爱他。良姨口沫飞过院门,指着满红:你肯为他死?你肯为他死吗?你死给我看!你敢死我就把他送给你!
满红街也不逛了,谁也不知道她转身回家真喝了一瓶农药。
水娣赶到卫生院去看她时,她已经走了。曾经在众人面前骄傲无畏的女子,正孤单地安静地躺在薄薄的被单之下,显得那么无足轻重。水娣擂着床板哭了一场。真傻啊!人家叫你死你就真死。一个无所畏惧的女子,似乎是让一句话给杀了。满红绝不是生无可恋的女人,她是这么热情的人,热烈地生活着的女人,历来以没心没肺来对无情无义的世界做最彻底的抗争。这样的女子,又怎么看也不是软弱可欺的人,怎么会这样莫名其妙地就去结果了自己?也许,这样义无返顾,不肯掩藏的爱,爱得近乎笨拙,傻到毫无防备,死神没有理由放过她。也许,她热情的表象之下是伤痕累累和疲惫不堪的心。也许她率直裸露的情感里覆盖了万般挣扎的极度疲惫。也许她就是涨势凌厉内心已伤得很脆弱的庄稼,禁不起轻轻一拔拉。水娣想满红到底做了她的替死鬼了。抬头看看院门外的小路,曾经走过的一些人已经永远消失了,那个走到那里就在那里高声大笑的女人再也不会从墙头出现,那个男人也被生活逼得远走他乡了,只有她一个人不为人知地担待着他们留下的暗伤。
洪水早退回了河床,水底的兽也睡着了,河面重新变得温柔清澈。经过清洁消毒,村子更干净了,只有洪水淹留的印迹,在墙面和树干上,等待风雨慢慢冲刷。
水娣揉着被阳光晃//www.czybx.com晕的眼,看着老姑把针在一块陈蜡上划拉,低头绣她没完没了的鞋垫。为了把心思从满红身上扯回来,她没话找话:
老姑,儿女可来看你?
不来的。老姑拖声说,顿了一下接着说:幼小的娃娃都抛弃了,这样的娘有什么好眷顾的。她像谴责别人似的,把这句在心里自我谴责了一辈子的话漠然地说出来。
可是毕竟是亲生娘啊。
我不仁在前,他们不义就怪不得喏。老姑为孩子白熊资讯网们解释道。
老姑像说别人的事情,淡淡的,手里一针一线有节奏地来回穿引着,不时把涩住的针在陈蜡上划拉。水娣想,老姑也是个死过一回的女人。
阳光暖烘烘,坐久了背脊上燥热,可退到屋荫下,不一会浑身又生寒,脚趾头开始刺痛起来,似乎冬天的空气里藏着无形的芒刺。
《鄱阳湖文艺》是由鄱阳县委宣传部主管,鄱阳县文联主办的连续性文艺期刊,欢迎作家、文学爱好者踊跃来稿。我们接收首发原创电子稿件,请不要一稿多投!(尤欢迎广大作家们以鄱阳湖、鄱阳元素为题材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)。
电子稿请投至杂志官方邮箱pywl2013@163.com,请在邮件的标题上注明投稿的文题,注明字数和作者名字。
三个月内未收到回复,稿件可自行处理!
稿酬从优。
内容版权声明:除非注明原创否则皆为转载,再次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文章标题: 脚趾头裂口子怎么办

